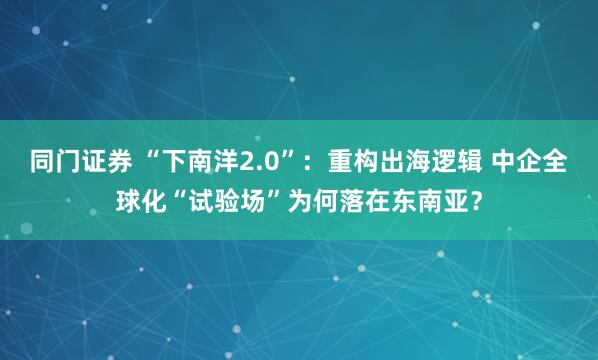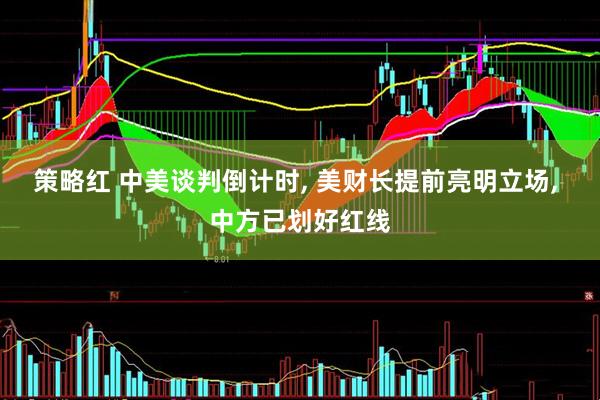在1974年,Steven Lukes出版了《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下简称《权力》)一书。甫一出版,该书就对当时的政治科学界关于权力的争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近50年后的2021年,该书的第三版出版,内容几乎是原书的5倍,包含了作者在第一版之后对权力问题的更进一步的反思以及对许多批评的回应。尽管第三版对原本的立场做出了不小的保留,但作者仍然坚持他近50年前对权力的理解,并试图论证这一理解不仅仍然优于其他的提案,更能为未来的研究项目如power cube提供指引(186)[2]。
但正如作者慷慨地展示给我们的(16),他关于权力的概念化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而在随后的版本中他也试图对其中的一些进行回应。在这些困境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两条:权力的第三维对人的“实际利益”的假定,以及他多次被迫承认的对他原本论证的规模的窄化。“实际利益”是一个充斥着历史包袱的概念,无论是在冷战盛期的1974年还是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2021年都不是个受欢迎的想法,而Lukes在各个版本中也不断地以新的方式回应这个概念造成的挑战,以至于“实际利益”问题似乎是唯一一个贯穿《权力》的三个版本的共同主题——而且,在我看来,似乎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论证规模的窄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一开始对“权力”这个唬人的概念的雄心勃勃的宣称,再到后来仅仅关注作为支配的权力,甚至于有些评论者认为Lukes的论证已经和真正的权力毫无关联了(Morriss,2006)。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没有被Lukes充分地意识到:如果“实际利益”的假定的确是有问题的,如果Lukes的辩护是失败的,那么权力的第三维就必须被重新表述;如果权力的第三维仅仅适用于Lukes眼中的“支配”现象,如果依旧存在一些直觉上和权力有关,也似乎不应该排除出权力的领域的现象不能被Lukes的作为支配的权力把握,那么权力的第三维就必须被从一个更加充分的经验基础上被概念化。
将这两条思路结合,我将主张一种对权力的第三维的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和Lukes的定义将有着显著的区别。由于种种限制,在论证中我不会考虑我的定义的经验研究适用性,换句话说:一个概念是否能很容易地被实证科学所操作化只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对理论的内容的有效性无关(46)。我将首先分析“实际利益”的假定带来的问题,并指出迫使Lukes做出这一假定的理论根源:利益冲突的视角。接下来,我将沿着Lukes在论证中暗示过却没有进行实质性分析的另一个视角,责任的视角,结合Arendt关于权力和责任的论述,从一个新的,不需要假定“实际利益”的视角重新讨论权力的第三维度。在这一新的进路中,我将通过考察Lukes原本的定义所无法理解的顺从主义现象来展示,责任的视角不仅在理论和道德上无需做出成问题的“实际利益”的假设,也能对更广阔的经验现象提供洞见,尽管具体的操作化和经验研究应用仍旧需要另外专门进行探讨。
“实际利益”(real interest)与利益冲突的视角
《权力》一书中的权力的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被概括如下[3]:(1)权力的第一维: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在这个维度,权力表现为某人或某个利益集团对进入公共决策程序的某个事项的最终决策施加影响的能力。权力的第一维将进入程序的事项视为给定的。(2)权力的第二维:对何种事项进入公共决策程序的议程设置的能力。在这个维度,权力表现为某人或某个利益集团压制潜在的反抗和不满,阻止其进入公共决策程序的能力,从而将其排除在狭义上的政治体制之外。权力的第二维将前政治的反抗和不满视为给定的。(3)权力的第三维:影响人们将何种社会现象当作反抗和不满的理由的能力。在这个维度,权力表现为某人或某个利益集团通过塑造他人的信念和欲望,从而阻止他人将某些实际上不利于他们却有利于塑造他们信念和欲望的统治者的社会现象当作一个需要被政治地解决的问题。权力的第三维将个人的“实际利益”当作给定的。
“实际利益”的概念显然是极具争议的:Lukes极力试图证明它不会像某种版本的主义马克思那样导向对专制的辩护,并花费相当长的篇幅讨论各种可能的对人的“实际利益”的理解。在这些讨论中,一个矛盾是显然的:一方面,Lukes主张,权力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指称”(157)并“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价值预设交织”(34),而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的利益是什么……这是内在地有争议的”(85-86);但另一方面,Lukes又将权力定义为阻止人们“以自己的本性和判断支配自己的生活”(90)的能力,并试图论证即便是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政治与流动认同也必须“基于某个人性(nature)理论,预设一个真实客观的利益”,“在得到承认时一些基本的或真实的利益得到满足”(126)。然而,如果利益是“内在地有争议的”,它如何能是“真实客观的”?如果不同的政治主张提出不同的利益概念,却又宣称这些概念是基于“人的本性”的,难道这不是因为所谓的“真实客观的人的本性”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而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说身份政治需要假定得到承认时某些基本利益得到了满足是无意义的,因为在和“利益”,“人性”一样,“承认”一词也没有固定的指称,潜藏在“承认”这个标签下的是各种完全异质的社会行动——最明显的证据是,同一个行动对一些人是承认,对另一些人是拒绝承认——而我们不应该被它们共享的符号所蒙蔽。如果一个词“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指称”,对它的使用也不需要预设一个真实客观的指称对象,因为它可以指称多种截然不同的对象。[4]实际的情况更像是,在一系列“利益的候选人”中,不同的政治主张挑选出其中的一些当作“实际利益”,而随着一些新的政治主张的出现——如后现代主义——一些新的元素被加入原先的集合,使得原先没有被任何政治主张当作利益的人的面向被当作了利益,而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预先假定政治思想的未来发展不会揭示新的可能利益,“没有理由相信存在一个权威(canonical)的利益集合,它能够一锤定音地解决所有问题”(153)。更进一步:这些新的利益是“真实客观的”,还是只是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换句话说,它们是原本就潜藏在“人性”中,只是逐渐地被发现而已,还是其实是人的不同面向随着他身处的社会政治结构而被赋予不同的重要性,从而人的“实际利益”部分地由他的环境的要求所决定?很显然,“实际利益”的概念是非常成问题的。
正如上面的引文暗示的,Lukes并非没有发现“实际利益”的问题。如果没有“一锤定音”的实际利益,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停止说“实际”,“真实”,“客观”这样令人误解的话吗[5],难道利益不是社会建构的,并充满偶然性和可变性吗?但Lukes的回应却是令人费解的:“把实际利益仅仅当作因果解释,理论框架和方法的一部分,由它们所决定,而这些则是需要被辩护的”,从而,“如果你主张唯物主义的解释……那么实际利益就是物质利益”,“如果你……使用理性选择理论,那么实际利益就是最大利益(best interest)”(153),如此等等。似乎只要理论框架得到了辩护,对实际利益的理解也作为理论框架的一部分得到了辩护——似乎对理论框架的辩护不需要依赖于对实际利益的概念化的辩护。Lukes的回应显然是乞题的(beg the question):对实际利益的概念化的辩护先于,而非后于,对它所对应的理论框架的辩护,因为它所对应的理论框架是关于权力的分配和行使的理论框架,而在逻辑上,是权力被利益所定义,而不是利益被权力所定义——它被“人性”所定义。进一步,如果实际利益需要被辩护为“真实客观的”,难道这不需要它对应的理论框架被辩护为“真实客观的”吗,难道这不是预设了一个“真实客观的”权力的分配和行使的图景吗——而果真如此,权力又如何能是“本质上可争议的”呢,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它的“客观事实”?如果Lukes认为政治、道德、价值这些议题是本质上可争议的,那么它们根据定义就和“客观真实”毫无关系。
如果Lukes不得不面临如此困境,如果Lukes的回应显得是如此窘迫,那只是因为他在论证权力的第三维时粗疏地进行了一个逻辑跳跃,而正是这个逻辑跳跃使得他必须假设一个物一般的“实际利益”。实际上,所谓的权力的第三维只是对权力的第二维的一个深化,正如Lukes的论证只是对“有限制的对行为主义的批判”(29)的一个彻底化:权力的第二维无法看到“在社会中压制潜在的冲突的各种不同的方式”(64)。在第二维里,权力只能通过压制已经存在的不满来压制冲突;在第三维里,权力却可以通过避免不满的产生来压制冲突——然而,冲突又随即复活:作为“一个潜在的冲突,即行使权力的人的利益与那些被他们排除在外的人的实际利益的冲突”(33)。即便Lukes在几页之前就指出不应该“坚持权力必须包括实际的冲突”(31,我的强调),他却似乎始终无法脱离冲突本身来思考权力。一旦冲突成为必需,Lukes就必须首先确定冲突的两个利益,然后通过比较两者的不同来定义权力。这一结局某种意义上是由他的出发点决定的:从一开始,整个“权力争论”(power debate)就被束缚在冲突的视域下,从政治主张的冲突,到前政治的冲突,再到尚未成型的潜在冲突。但这里的“未成形”却没有被就其本身地考虑:Lukes没有思考这一模糊的,有待澄清和被意识到的维度意味着什么,而是直接把“模糊的”等同于“还没有被看到,但已经被不知怎的确定了的”,把缺席(absence)理解为另一种在场(another presence),然而他的论证只能导向缺席本身。换句话说,Lukes的论证能说明的只是:真正的冲突不是两个存在之间——一方的利益和另一方的“实际利益”——的冲突,而是存在和不存在的“冲突”:被支配的一方本应作为一个政治人存在,但他却被剥夺了成为一个政治人的权力;而成为一个政治人就是把所处的社会世界当作一个政治的世界,当作一个一切都需要被辩护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有权要求辩护的世界,一个理性的、言语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缄默的世界。第三维的权力能够“塑造信念和偏好……【或】绕过行动者的信念和偏好的塑造本身(注:即让权力的运作对受支配者而言完全无法被意识到)……【或】破坏人们以自己的本性和判断支配自己的生活的能力本身”(186)。所有这些所共有的,不是一个利益和另一个“实际利益”的冲突,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人存在,理性地塑造自己的信念和偏好,与无法作为政治人存在,被剥夺了自己提出政治主张的权力,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而“没有真正的政治主张”却并不等于“我的政治主张与我的实际利益的要求相悖”,不等于“我的实际利益所要求的政治主张没有被我意识到”。Lukes的逻辑跳跃就在于将这两者等同,而他之所以能够进行这一跳跃,只是因为他无法就其本身地理解这一“否定性的现象”,因为他的利益冲突的视角决定了他必须始终将权力定位在肯定的(positive)利益之间的比较上。然而,不是我的表面上的政治主张和实际利益要求的政治主张相悖,而是我根本没有真正的政治主张;不是一个实体和另一个实体的差异这一“肯定事实”,而是一个存在的维度的缺失这样的“否定事实”。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责任的缺失更好地体现了这一否定事实的含义:当我的信念和欲望是由统治者所塑造时,为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负责的不是我,而是统治者。实际上,如果Lukes通过这一逻辑跳跃导向的不是一个内在融贯的错误结论,而是一个充斥着“本质上的可争议性”和“真实客观”的矛盾的权力概念,这意味着在一些方面他成功地把握到了权力的第三维的真正含义,只是他并不是那么一以贯之。这就是他对权力和责任之间的联系的强调:“定位权力就是定位责任”(63),以至于有些时候一些群体“是有权力的,因为他们是有责任的(powerful because responsible)”(72)。我们已经看到,从利益冲突的视角出发,权力的第三维似乎必须预设一个“实际利益”,以和受支配者实际追求的利益相冲突;但当我们从责任的视角出发,一切都不一样了:权力的第三维指的是被排除出责任的领域,被剥夺负责任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以及被剥夺要求他人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在受权力的第三维支配的情况下,受支配者并没有按行动一词的全部意义行动,因为他不负责任——因为他无所谓有责任与否,正如一块石头、一棵小草无所谓有责任与否。他不是个负责任的存在者。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人是否负责任,是否进入了政治的领域、行动的领域、责任的领域;在此之后,才有真正的政治冲突。不是责任基于利益,责任不是来源于我的某个行动增长了我的利益却破坏了其他人的利益,而是利益基于责任,只有我完全地为我的行动负责了,行动的结果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因为只有这时我的行动才是恰当地属于我的(properly mine)[6]。
“顺从主义”(comformism)与责任的视角
遗憾的是,Lukes在《权力》中并未对责任概念展开任何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尽管“责任和权力的联系是解决后两个问题(注:即未预料的后果是否算是权力以及如何确定集体权力和结构决定的边界的问题)的关键”[7](62)。在另一些本应结合责任进行讨论的场合,如对自主性(autonomy)的讨论(40-41),Lukes也没有看到责任的相关性[8],尽管对康德而言——讽刺的是,Lukes在书中曾多次引用康德——自主性、责任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也许更加讽刺的是,一位Lukes曾专门讨论并(自我意识良好地)反驳了的理论家恰恰提供了一条从责任的角度重新思考权力和政治的思路:Arendt。
让我们首先处理Lukes对Arendt的讨论。在一长串的——标志着Lukes并没有真正理解Arendt的原意的——直接引用后(很有趣的是,Lukes对Arendt的直接引用要远多于对帕森斯的直接引用),Lukes评价道,这仅仅是“power to,而忽视了power over(注:前者是造成某种结果的能力,类似causal force,后者是支配他人的能力,不仅是因果的,也是社会的)……因此,权力的冲突面向,即权力是施加在他人之上(over)的,从视野中消失了,与之消失的也有我们一开始试图理解权力关系的核心兴趣所在”(39),并且,这一定义只是为了“加固特定的理论立场,但他们所试图说的一切也能在我们的框架下更加清晰地表述出来……Arendt想要说一起行动的群体成员在行使着权力……【这些“权力”】在我们的框架中被看作影响(influence)而非权力(power)。帕森斯和Arendt想要关于一致行动所说的一切仍然是可说的,但我们却还可以用权力的语言说那些他们反倒想移除出权力的语言的那些现象”(39-40)。在Lukes的概念地图(41)中,影响(influence)指的是得到许可(sanction)的他人对我的影响(effect)。顺带一提,这张概念地图仍然是沿着利益冲突与否——因为Lukes的讨论总是局限在利益冲突的视角——和是否得到许可——因为权力的第三维涉及到未经许可的权力作用——这两条轴线展开。
问题的关键在于,power to和power over完全是从个人的角度定义的:不论是达尔的“符合直觉的权力观”(27)还是斯宾诺莎的potentia和posestas(78),都是从个体出发的;而权力也随即被定义为一个倾向属性(dispositional property),属于个人。相反,Arendt的权力却是一个涌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y):“权力从来不是个体的属性,它属于群体,并且只要群体依旧成其为一个群体,权力就始终存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说起一个有权力的人时,我们只不过是从比喻意义上使用权力一词”(Arendt,1970:44)。并且,Arendt非常有意识地将她的权力概念与Lukes所处的政治哲学传统对权力的理解对立,在后者看来“权力是统治的工具……一个人把自己强加在他人身上并让他人成为自己意志的工具”(Arendt,1970:36),从而“最关键的政治问题一直是谁统治谁的问题……但只有当我们不再把公共事务还原为支配关系时,人类事务的原本样貌才会展现出它们的多样性”(Arendt,1970:43-44)。权力不等于统治,而法律也不等于命令,因为法治(rule of law)不是人的统治(rule of man over man),后者只是“适合于奴隶的政府”(Arendt,1970:40)。对人的服从被对法律的支持所取代,而这一支持“从来不是不加质疑的”,只有暴力(violence)才可能导致不加质疑的同意,例如“当罪犯在刀枪的威吓下抢劫时能施加的那样”(Arendt九融配资端,1970:41)。
为了更清晰地阐明Arendt的权力概念,让我们考察一下她着力强调的权力(power)和暴力(violence)的对立。“最极端的权力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而最极端的暴力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Arendt,1970:42)。在Arendt看来,权力完全取决于一个(并非不加质疑地)支持共同生活的秩序的群体规模,“政府的权力依赖数量”(Arendt,1970:41),而暴力却仅仅依赖于暴力的工具,它在原则上可以仅仅由一个人掌握,却依旧有着强大的力量——尽管当下的暴力机器仍需要军队的配合,也就需要“统治者内部的团结”的权力,但“机器人士兵的发展……可以改变权力对暴力的优势”(Arendt,1970:50)。暴力是个我们在日常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无比熟悉的概念,或至少Lukes的论述已经让我们对它熟悉了,但Arendt的权力概念却包含更多微妙之处。让我们结合一个例子说明一下。
当公共秩序被少数人破坏时,不是“少数人通过暴力成功了……而是大多数人拒绝使用权力去压倒破坏者……没有人愿意为现状(status quo)付出多于仪式性的服从,政府所面对的是巨大的否定性的统一体(immense negative unity)”,“少数人的权力比起民意调查显示的要多得多,因为观望的大多数人……已经是少数人的潜在同盟”(Arendt,1970:42)在这个例子中,自主地离开或被动地被排除出政治领域的冷漠的大多数是根本没有权力可言的,they are totally out of the game,因为他们并没有(并非不加质疑地)真正地支持现状,他们放弃了在政治舞台上做出真正行动的权力,当巨变发生时,他们的意见从来都不重要,直到他们真正选边站。Lukes也分析过类似的例子,“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再遵循仪式而灭亡的,而只是在社会活动家组织的运动强大到争取到并转变了大多数警觉的顺从主义者(comformits)后才灭亡的”(Ost,2018,转引自173),“这只是一个大家一起玩的假装遵奉官方叙事的游戏……但已经没有任何的真信者了,没有人再被体制所愚弄了”(173)。在这里,这些冷漠的日子人[9]和社会活动家所发挥的政治影响之间的区别是显著的:前者的失去信仰并不会导致政权的崩溃,而后者才是对统治的真正威胁。但日子人和真信者显然也是不同的,对真信者而言,Lukes的权力的第三维所给出的“信念和欲望被统治者塑造”的诊断也许是合理的,但日子人却更像是Scott口中的埃塞俄比亚农民,“避免任何明显的不服从的举动,却也在反抗中发现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通过进行避免公开对抗却又能抵抗权威结构的反抗实现”(Scott,1990:86,转引自132)。Lukes的结论是,他口中的权力的第三维和在这里压迫埃塞俄比亚农民的权力可以共存,因为社会足够复杂,容得下真信者和日子人共存,因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完全把握……那些让支配的现状显得可理解,可容忍,不可容忍,或甚至可欲(desirable)的日常的假定”(136-137)。在这里,Lukes的权力概念的适用范围被进一步缩小,不仅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缩小到作为支配的权力,更是缩小到仅仅适用于造就了所谓“厚的”(thick)虚假意识的支配,而完全无法应用于仅仅造就了“薄的”(thin)虚假意识——即仅仅让人们觉得现状虽然不好,但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而放弃反抗——的支配(Scott,1990:72,转引自131)。从Lukes版本的权力的第三维出发,甚至完全无法理解埃塞俄比亚农民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杂货店主的所作所为:他们有不满,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实际利益”受损了,但这种不满却又是完全非政治化的,没有任何驱动他们政治地反抗现状——而不是仅仅把压迫当作仿佛人生“不得不”面对的逆境,仿佛世界和人性就是这样,仿佛it is just the way things work!——的动力。这是完全无法被基于利益冲突的权力概念所把握的:从利益冲突出发,权力只能作为影响信念和欲望的能力,或影响基于信念和欲望产生的政治主张被纳入议程并得到合适的解决的能力;它从来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人们有“合乎自己实际利益”的信念和欲望,却不会为此提出任何政治主张,不会“把个人的当作是政治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处在权力的二维三维之间的特例:it is a rule!我们的日常政治经验无不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反常的、特殊的情形,而是压迫的新的,有其独特含义的形式。说它处在权力的二三维之间只是逃避了对它进行真正分析的问题。当Lukes批评Arendt将过多的东西“排除出权力的语言”时(40),我们却发现,是Lukes自己将如此明显的,在当代如此重要的一种现象剥夺了任何的从权力的角度理解的可能性,并甚至剥夺了任何就其本身的独特性进行理解的可能性。简言之:Lukes的权力概念无法理解顺从主义(comformism)。而Arendt的权力概念,通过把权力定位在那些真正地支持某个政治主张并为此集体地行动的群体中,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压迫形式的真正含义:将被压迫者完全排除出权力的领域,也就是政治行动的领域。
从责任的视角能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说拥有“薄的”虚假意识的受压迫者没有权力,无法进行任何政治行动,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形成一个政治化的群体,也就等于说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当权力解体时,革命是可能的却不是必然的……即便权力已经在社会运动的街头展露无遗了,那些为了这个目的行动的人仍然需要去承担他们造就的政治结果的责任”(Arendt,1970:49),否则革命就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人准备好接受权力和相伴的责任”(Arendt,1970:50)。权力来自人们聚集起来,自觉地,并非毫不质疑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行动时拥有的力量,而一旦这个目的是被自觉地达到的,每个人都需要为此负责——也只有当每个人都为此负责时,目的才是可能被达到的,否则革命最后建立起的不过是又一个少数人的基于暴力(violence)的统治,否则那些表面上的“革命群众”不过是另一种顺从主义者,顺从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的革命却并没有真正做好为此承担责任的准备。一个真正有权力的集体不是一个由少数团结的统治者和大多数顺从主义者组成的——更极端地,“恐怖统治的有效性几乎完全依赖于社会原子化的程度”(Arendt,1970:55)——而是一个所有人都真正地,并非不加质疑地集体行动的集体,一个一切人对一切人负责的集体。一切人对一切人负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把其他人的处境和行动当作和自己有关的事情,自己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的事情,真切地产生一种共同命运的体验。在政治行动中,没有人再置身事外,每个人都充分意识到自身命运和政治行动的结果的关联。所谓的所有人“一起行动(act in concert)”(Arendt,1970:49),不只是说他们在做同一件事,而且是在说:每个人在这个集体事业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时,始终是有意识地把他人放在行动的背景中的,总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选择和命运放在集体的选择和命运中的,总是内在地和他人一起行动的(inherently acting with others),他的行动内在地蕴含了一个平等的他者。这里的行动的模型,不是斯宾诺莎式的作为原因造成某个结果的,定位在个体上的行动,而更类似于对话(dialogue):在对话中,如果不是每个人都speak according to others,对话就不可能进行;如果不是对一个在理性上平等的他者说出的,那么我的言语就根本不是对话的一部分;而所有人所共同担负的责任,就类似于所有对话者对于对话的进行所担负的责任,在其中个体和他者不可能得到清晰的区分。
那么,权力的最深刻的维度就不是塑造被压迫者的信念和欲望,而是让他没有能力进行对话——让他没有能力真正意义上地和他人一起行动。当他没有能力以一种内在地蕴含着他者的方式行动时,当他的行动外在于他者,也便外在于社会时,社会便成了“物”,外在于他,以一种独特的客观性强迫个体必须按照它规定的模式生活。受压迫者从来没有在真正地意义上活在社会之中;他始终外在于社会,就像一个物理实体外在于他所处的物理环境,仅仅被动地受后者的形塑。他感觉到了不满,但他的不满就仿佛动物对多变的自然环境的“不满”,其中并没有包含任何造成他不满的源头其实并不外在于他的观念,并没有任何他需要为他的社会担负责任的观念,也就没有任何处在社会中的他拥有着他的社会性带来的权力的观念。他被排除出政治的、行动的、责任的、权力的、对话的领域:他不是一个集体的政治人而是一个个体的自然人,不是一个主动的行动者而是一个被动的受影响者(the affected),不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人而是一个无所谓责任的人——他对“他的”社会不负责任,正如我们对几万光年外的天文学现象不负责任——,不是一个有阿伦特式权力的人而是一个只有斯宾诺莎式权力的人,不是一个对话者而是一个缄默的“自由因”。而政治、行动、责任、权力、对话这些概念,都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指向同一个现象而已:the meaning of living together。
政治与非政治之间
让我们总结一下至此为止的论证思路。首先我们发现Lukes的“实际利益”概念引发了一系列他并未令人满意地处理的问题。但实际上,Lukes的论证本身并不需要他承认一个成问题的“实际利益”;“实际利益”概念的表面上的必要性来自于一个逻辑跳跃,从“缺乏真正的政治主张”跳跃到“有意识地追求的政治主张和实际利益要求的政治主张之间是矛盾的”;这个逻辑跳跃揭示了Lukes未言明的预设:仅仅以利益冲突定义权力。回到跳跃之前,我们发现,从责任的角度能够避免逻辑漏洞以及假定“实际利益”的存在:权力的第三维指的是将受压迫者排除出责任的领域。Lukes尽管对此做出了一些暗示,却并未对责任概念和责任与权力的关系进行实质上的分析。我主张,可以通过Arendt的权力概念对此进行澄清。尽管Lukes在书中对Arendt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却是建立在他完全没有理解清楚Arendt的基础上的:Arendt的权力是群体的属性,而Lukes的是个体的属性,两者的进路完全不同。在对Arendt关于顺从主义的分析进行考察时,我们不仅发现了Lukes的权力概念在这个当代极为重要的政治现象上的完全的不适用性,而且由此对权力和责任的概念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澄清。由此,权力被和集体行动联系起来,在集体行动中每个人的行动都内在地蕴含着其他平等的个体。“对话”可以当作一个思考这种行动的模型。在集体行动中,每个人都要为了集体行动的社会后果负责,也就是为一同行动的其他人负责,为整个社会的未来负责。权力的第三维通过使得受压迫者失去进行任何集体行动的能力,使得他的行动无法蕴含平等的他者,从而使得社会现象完全外在于他,社会自身的运转是他需要适应的,但他却不必为这一运转本身负责,因为社会与他无关。他没有权力,因为他并不处在政治的领域,因为他并不以政治人的方式存在,一句话,因为他没有责任,因为他并不在真正的意义上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
因此,权力的第三维并不运作在受压迫者的“实际利益”和统治者的利益之间,而是运作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这里的政治和非政治指的不是狭义的政治制度内外,而是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权力的第三维的运作使得一部分人无法以政治人的方式存在——比如,通过对社会化过程和信息获取的管制——,使得他们在所生活的世界里看不到任何政治性的东西,使得他们没有“政治学的想象力”。权力的第一、二维则运作在政治人的存在方式之内:权力的第二维使得政治人无法被政治制度接纳,权力的第一维使得处在政治制度内的政治人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减弱。但不论如何,权力的一、二维都假定了:人们以及作为一个政治人,提出真正的政治诉求了。权力的第三维的真正的激进性不在于对“实际利益”的宣称,而是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和挑战:人不是天生的政治人,人的政治面向需要被培育,政治对所有人的开放性需要被保护;而离开了政治、权力和集体行动,就无所谓责任和道德。
参考文献
[1]: Arendt, H. (1970). On Violenc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2]: Hochschild, A. (2012).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Lukes, Steven. (2021). Power: A Radical View. Red Global Press.
[4]: Milgram, S.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 Abnorm. Psychol. 67, 371–378. Morriss, P. (2006). Steven Lukes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Political Study Review: 2006 vol 4, 124–135
[5]: Morriss, P. (2006). Steven Lukes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Political Study Review: 2006 vol 4, 124–135
[6]: Morriss, P. (2006). Steven Lukes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Political Study Review: 2006 vol 4, 124–135 Quine, W.V.O. 1948. On What There Is. Review of Metaphysics. 2(5): 21–36.
[7]: Ost, D. (2018). The Sham, and the Damage, of “Living in Truth”,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32(2): 301–9.
[8]: Scott, J.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 在引用中,出于简洁,若出现括号内无作者姓和年份,只有页码的情况,一律默认为引自Lukes, S. (2021). Power: A Radical View. Red Global Press。另外,文中所引英文文献均对应英文版页码,翻译由本人进行。
[2] 鉴于《权力》第一版的主要内容已经在课堂上介绍过了,在正文中我对已经讲授过的内容将快速带过,不浪费笔墨详加考察。
[3] 在第二版以后,Lukes部分修正了他原本的论证,并将他对权力的定义局限于“作为支配(domination)的权力”。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忽视这一区分,依然使用“权力”一词,不仅因为Lukes本人的讨论基本只局限在作为支配的权力,也因为支配的确是“许多权力的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115)。
[4] 在这些雄辩术(rhetoric)之外,一个严格的证明可以参见蒯因的著名论断:“没有无同一性的实体”(there is no entity without identity),即,如果对一个假设存在的实体,不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唯一的一个对象和它同一,如果它和多个对象同一,那么那个假设存在的实体其实是不存在的。(参见Quine,1948)
[5] 把“被一个社会所广泛接受”等同于“客观性”只是在扰乱视听,文化所具有的主体间性地位当然意味着它不是个人的,不是“主观的”——但它也不是“客观的”。真正要做的不是满足于把“非主观性”的东西都归为客观的,而是思考这种独属于文化和社会的“客观性”。Lukes的“一锤定音”(the last word)的理念很好地表达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不在于一个东西是不是主观的,而是在于它有没有决定性的(conclusive)答案;权力、利益等等当然不是主观的,但它们——根据Lukes的说法——也没有决定性的答案。这是我通过拒绝把它们称为“真实客观的”想要强调的。
[6] 这并不完全是哲学思辨的“空想”(尽管真正的哲学思辨从来不是空想)。许多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当个体被要求不质疑地服从命令行动时,他们会感到(1)自己的动作“仿佛不是自己做出的”,(2)自己对行动的结果不负责任。(Milgram,1963)情感社会学的研究也有类似的例子:服务业的劳动者感觉自己的笑容仿佛不属于自己。(例如,Hochschild,2012)
[7]顺带一提,这两个相当重要的理论问题最后仅仅被打发给了权力和责任的联系,仅仅在这一个地方看似做出了解决,但Lukes却根本没有分析这一联系的含义。这也是一个支持我们朝责任的方向探索的证据。
[8] 再顺带一提,也许是由于没有结合责任的缘故,在自主性的讨论中Lukes也留下了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说服他人算不算权力,以增进他人的利益的方式支配他人算不算权力?Lukes并没有以任何实质性的讨论处理这些问题:他似乎满足于承认“他没有看到任何解决这一二律背反的途径,这里运作有相互矛盾的概念压力”(41)。但难道这不是很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矛盾吗?
[9] “日子人”的说法也许不准确,但我没有找到更加合适的用词。我想表达的意思是,(1)一方面,借用Lukes所引用的哈维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杂货店主的描述,“他把共产党的宣传标语贴在窗上,只是因为同样的标语已经在那停留了无数年了,只是因为所有人都这么做,只是因为这是他必须做的。如果他不服从,他就会面对麻烦,被指责说没有恰当地装饰他的窗户,甚至对党不忠。他这样做,只是因为如果想要生活,这些事就是必须做的。这是为了维持一个宁静的生活,与社会保持和谐,所需要做的几千件事之一。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他的。”(Havel,359,转引自172)(2)另一方面,这位店主,正如一些哈维尔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不能被认为是完全被动的服从者;他只是完全没有权力而已,但只要统治出现松动九融配资端,他依然是新社会运动的潜在同盟者,至少不会是统治者的维护者。(173)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大牛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升宏网 最高法院9号指导性案例不再参照的理解与适用
- 下一篇:没有了